目前访问量:124815
散文“年贺状与飞帖”
散文《年贺状与飞帖》
作者:李永亮 / 诵读:笑笑
作者:李永亮 / 诵读:笑笑
日本的”年贺状”和中国的”飞帖”,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,但他们之间却似乎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。
每年的元旦前夕,在日本电视新闻的栏目里,主持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新年的倒计时日,而在这样的时刻我也总是平静地坐在桌前,整理着往年收到的年贺状。在这一枚又一枚的年贺状里,蕴藏的是情深意长的祝福,书写的是富有个性的文字和图案,看着年年增多的年贺状,它们几乎成了我难得而又珍贵的收藏品。
:
在我收藏的年贺状里,当然大部分是来自我的日本友人,他们中既有国会议员,大公司的老板,还有律师,教师,平民百姓商店街蔬菜铺的主人….在印刷体的新年贺词以外,他们通常都会另外用笔,写上一句两句鼓励的话语。抚摸着年贺状上的字迹,似乎能感受到他们情真意切的温度,透过年贺状的纸片,我仿佛又能看见他们的亲切与善意。在我生命的旅途中,曾经得到过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和支持,特别是我遇到困难、面临危机的时候。
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可以跨越语言和国界的,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情感的沟通,更需要的是要依靠实物的载体来实现。我不能不说,年贺状是一项伟大的发明
尽管社会阶层.职业各有不同,但在年贺状的世界里,应该一律都是平等的。我的年贺状收藏之所以显得珍贵,是因为他们还是一种纪念。在我的日本友人中间有的可能会来往多一些,有的少一些,而有的甚至于几年都见不上一回面,但全凭着一枚薄薄的年贺状连接着彼此的挂念。
如果说人生有什么遗憾或是伤感的事情,那就是有几位我尊敬的友人,在这几年里不幸地相继去世了。我还清晰的记得追悼会上的情景,但他们以前寄来的年贺状,倒也成了一种永恒的纪念。
年贺状的弥足珍贵,还在于它是一种忠实的记录。我在日本三十多年的时间里,曾经有过五次大的搬迁。以前住在什么地方,我大概可以脱口而出,但具体到几丁目几番地,我的记忆就好像断片停摆了。
然而,年贺状记得。在我收藏的年贺状里,准确地记载着我过去的,曾经停留过的驿站:一个遥远的地方。从东京板桥区仲宿的一条小河出发,到川崎市麻生区的新百合之丘,接着又在同市的幸区北加濑住了八年,然后转到横滨的绿区东本乡,最后在西东京的药师池边上找到了理想的定居所在。
可以毫不隐瞒地说,我的每一次迁移,都曾经得到了日本友人无私而又热情的帮助。这大概就是我把年贺状的珍贵视作为“古董”收藏的原因吧。
日本年贺状的风俗习惯,听说开始于明治维新时代。邮政制度的建立,让人们之间的交往有了新的仪式感。而在中国,据传宋代时有一种过年的祝福形式称之为“飞帖”。家家户户在门口上贴上一个接福的口袋,用于盛装邻里乡亲送来的“飞帖”。
“飞帖”二字,是我熟悉的汉语中最为生动,最为美丽的单词,可惜现在能够记得“飞帖”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了。如果是这样,那么瞬间即逝的微信,可能就是“飞帖”的现代版了。
在今后的岁月里,无论是阳历的日本新年,还是阴历的中国春节,我都将会一如既往地用有形的或无形的文字,向我远方的朋友送上自己一份小小的祝福。
我不知道日本的年贺状能否寄往中国,我也不知道年贺状上是否盖有飞帖的邮戳,但我看到,大年初一的凌晨,日本全国的邮递员整体出动,他们挨家挨户地分发着祝福的年贺状,这是何等巍蔚壮观的景象啊!
我想象:那一枚枚的年贺状,就像是漫天飞舞的雪花,在空中,在冥冥中护佑着我们,它们在传递亲情的同时,莫非还是我们平民百姓心中的“萨德”,能够大概率地抵御着外来的“不祥之物”,和抗击肆虐妄为的“病毒”。
健康与安宁,但愿人长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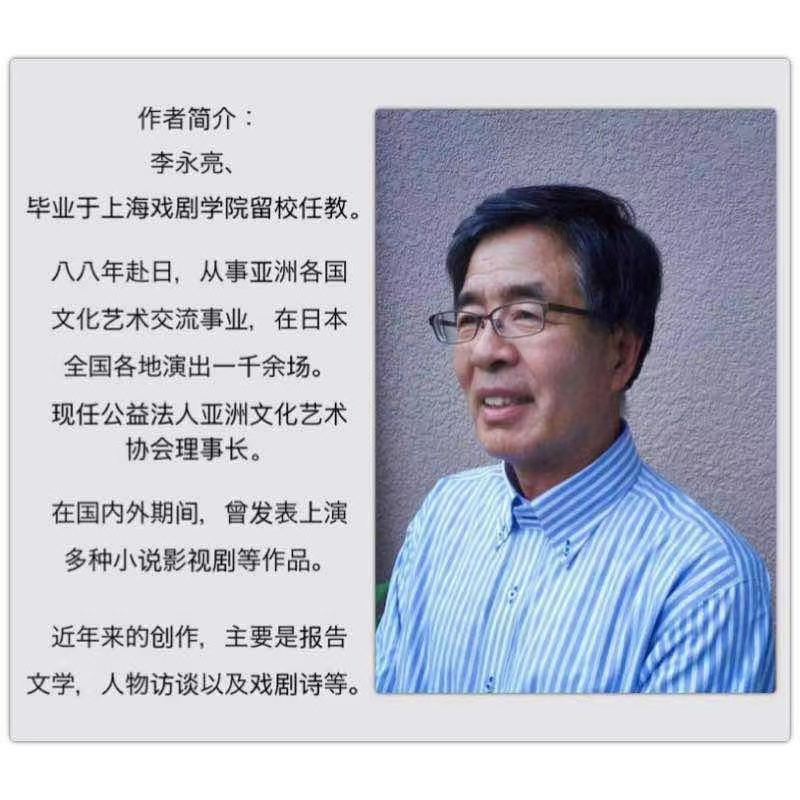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#{{item.rowno}} {{item.content}}
{{item.reg_date | date}} {{item.acc}} {{item.ref}}